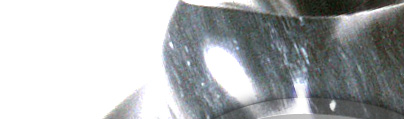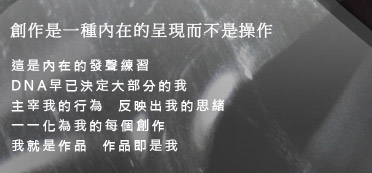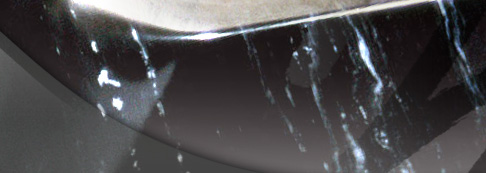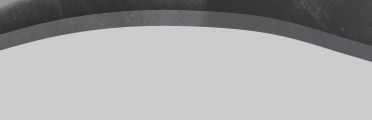當代台灣的現代藝術,長期存在著去貼近、追隨美國、日本當代藝術風潮的傾向。此一現象猶如將藝術視為如時尚工業,可以藉由聽任外部環境的壓力形成一般,在時尚工業中,流行是由少數的知名大師所決定,其後則由一群跟隨知名大師的二流人才對既定的流行趨勢進行頂禮膜拜般的再確認與傳播,也因此時尚現象其實就是大眾追隨著由少數人決定規則的趨勢。然則這樣時尚地藝術作品卻無法長久的受人欣賞,並且讓其價值依舊歷久彌新,而僅能是如我們欣賞時尚表演一般,將這類的作品相較於觀賞偉大藝術品所產生的感動,其所帶來的感動,更僅是微不足道的心緒激動而以。
藝術,精確地來說,其僅誕生於天才般的創意及激昂原創性的神聖領域之中。台灣,藝術自性方才剛剛開始綻放。
儘管年輕、活力旺盛且經濟繁榮台灣人卻深受僵化的教育制度之害,在這制度下其訴求的是將人塑造成為一個高所得的追求者而非一個具有自我、原創思考的思考者。僵化的教育制也同樣地存在於藝術教育之中,其僅重於強調技法、技巧的高度純熟,而非具有氣質及靈思妙想的表現。以音樂為例,每年總有數十位年輕的台灣新生代,讓西方音樂家對他們純熟的技巧以及完美的演奏感到吃驚詫異,然則其音樂本身卻僅帶來些許的移情而已。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在教育過程中通常將藝術視為一種競技∼以完美的演奏、表演贏得獎項、頭銜為目標。
侯連秦,一位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創作者,其作品展現出充分的天賦。侯連秦像是來自另一個國度的人,來自一個「美光」永遠不朽的時空!他的作品充分洋溢著對於高尚、美與優雅的歌頌,甚至透露著幽默和風趣。從他最近的台中展覽所挑選出來的作品看來,已然展現出宛如大師般的風範,作者對於三度空間的體積、二度空間平面與物象表面的掌握不但游仞有餘,毫不生澀,對於簡約的形式追求也大膽而直接。觀者幾乎難以置信這些作品是出自一位害羞的台南藝術學院的研究所新生,儘管剛完成他在研究所的第一學期課程,然則藝術家已透過其創作悄然的將台灣文化的樣貌提升至國際的舞台上。
傳統上,雕塑這門藝術在泛太平洋文化區,包括美洲印地安部落、太平洋內諸島、中國、日本、韓國,一直是重於平面表現的,換句話說,是長於二度空間透過線條的流動來呈現正面的形式與表情。但是在西方它從早就有三度空間的傾向,從金字塔到充滿著動態的人物雕刻,卻是一項古老而光輝的傳統,它可以遠溯至古埃及或愛琴海時代的島嶼文化繼之是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明,希臘的石雕極早就以其自然流美的線條,達到別的文化中不曾見到的立體石雕的完美形象和藝術上難以企及的高峰,它既表達了人體栩栩如生的生動,也蘊含著藝術家的情感。時至今日,任何一個歐洲人,只要走在(沒有在二世大戰被轟炸的都市中)大街上,更不用說進入美術館或大教堂?,舉目所見都是他們所熟悉的這種在歐洲有深厚傳統的立體雕塑作品。
和西方的情況很不相同,在泛太平洋、特別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區域?,藝術的重心則表現在平面的繪畫?,東方的傳統不僅強調〝古法用筆〞,線條也一直是所有藝術表現中的神髓。而東方的雕塑觀念,基本上是較扁平而正面地向前方發展的,就像是把繪畫轉換成固體形式一般,不過是將平面物體加上了厚度的延伸罷了。因此我們有商代的殉葬人物雕像,其扁平感有如用作餅乾的模具蓋出來似的,又如南太平洋的復活島上的人像附屬於巨大的石塊之上,或如美洲印地安土著的或淺或深的木雕圖騰柱,這些文化基本上對物體在三度空間的呈現都是將平面上的線條加以雕刻,而不是由大石或巨木中釋放出一個在三度空間扭曲飛動、其面面皆一樣活躍的立體物。即便是在東亞佛教雕刻進入所謂的〝寫實〞階段,佛像的面部、衣紋都呈凹凸起伏之形式時,仍然都為正面而看。
因此侯連秦之出現於台灣更是不尋常中之不尋常。設想他幼小生長及日常生活的環境舉目所見都是台灣廟宇神壇中那些扁平的雕像,以及嚴肅至極、面孔朝前方正視的政治人物銅鑄立像,而他竟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出發自內心的、非常純粹的對物體在三度空間的熱愛與熟識。
侯連秦在一九八一年出生於高雄的一個工人之家。從小他就從畫冊中看到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大為喜歡。而從書上、電視上觀察到海洋生物的形狀,更令他著迷。他一直渴望學會潛水,希望有朝一日能深入海底那神秘的世界,探索在深海的重重激流中沖刷激盪下轉動漂浮不已的生物動態,侯連秦在板橋就讀台灣藝術大學時專攻雕塑,當時看到台南藝術學院研究所畢業的學生竟能把大理石那種堅硬的石材變成如液體般流轉的形狀使他大受啟發,決心要一探究竟,專心深入地研究來表現物體在空間柔性流動的感覺。我們得感謝這個大眾媒體無所不在的時代,它使得意象的傳播無遠弗屆,到達世界各個角落,因之台灣的年輕藝術家侯連秦不用生活於義大利的佛羅倫斯,一樣可以感受到石材在空間默然運轉時所散發出的活力。
在不到一立方公尺的作品中,侯連秦的大理石作品卻能夠散發出一種巨大、紀念碑式的觸覺與氛圍。他的作品多數是發光且光滑的,它們抽象性的曲面上到處閃爍著光滑的肌理,又能引起動態感。一個他還得注意的挑戰是在大理石黑白交錯的不同層次中,其內部的結晶與紋理同時能自動地給予人強烈的召喚,訴說著一種鮮明的自我生命意識。的確,某些作品中,它們輕鬆隨意的攀附或伸展於大理石光滑的表面,如同是在與藝術家追逐、玩耍、嬉戲…另一方面,也對藝術家造成一種形式上不能忽略的挑戰。在此場侯氏的初次公開展覽中,這種缺點不影響到作品本身超然的藝術價值和永續保傳的潛能。尤其神奇的是這些作品具有隨著觀者角度和想像力而「改變其形式」的能力。但是正如所有具有永續價值的美好藝術作品一般,一旦離開藝術家的工作臺,它們便會取得自身獨立的生命,也會以它們獨特的魅力,觸動觀者內心深處隱匿的赤子之心、甚或鼓舞、溫暖人心,把觀者推向一個深沉未知的冥思之境。
在展出作品中有一件珊瑚色作品〝提〞,作品的整體以自由發展形式為基礎,在其厚重流動的塊體中羞怯地浮現微小的突起,連帶的將視覺引入那流動跨越作品表面的深色紋理中。受作品其自身珊瑚色的炙熱感以及造型、紋理的流動感;一種猶如奶油融化於炙熱的平底鍋一般從塊體的邊緣處翻湧蔓延,而依舊保持其表面的張力質感的感覺油然而生,這件作品以形體引發觀者將自身的認知經驗與想像連結。
〝海的記憶〞,這是一件緊緊往內合抱、白色卵形卻具有兩耳(或兩臂)的作品,它一方面雖然有趨於極內向之傾向,另一方面卻似乎又欲爆發出壓抑不住的歡愉。它的緊密處像一顆蛤蜊,然而在它的形體內外,卻有種微妙的扭轉力量,分別從幾個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等級的張力互相推擠與膨脹,彷彿與它底下海床生息起伏的韻律,默默地產生和諧地呼應及共鳴。從一端看來,觀者看到的是一個有耳、鼓漲(或背部隆起)的橢圓形,尾部突出,從另一端觀之,則一切張力轉移又到另一個方向,與先前的觀看經驗略有不同,而從短的這角度視之,此作品幾乎呈現出幽默而自我滿足的半球形。
侯連秦在2002到2003的早期作品中,溫柔地喚起海洋的意象,同時也受他自己視覺與觸覺經驗的感發觸動。雖然這些作品已呈現抽象的傾向,其內在結構的份量顯然超過具體的海洋生物意象,但它們的產生與海洋的靈感畢竟尚未脫掉聯想關係,它們仍然多少懷著些「模擬性」(mimesis)。
在創作一系列可喚起觀者對海洋生物想像的具象形體之後,侯連秦開始朝解構可辨識具象形體的方向發展。新的創作形態發展可以一件黑色紀念碑式的作品為例,〝對摺〞此作品形體猶如柱體與平板交錯擠壓而出,並存著筆直與彎曲的作品側面。從作品的表現中可明顯的看出其形態的源流並非來自於受海洋生物的啟發或影響,而無寧更是平面以及曲面彼此交織的情詩。儘管面對新形體的創作挑戰,其結果依然表現出細緻的流暢性以及典雅的單純性。在此作品中,白色紋理再一次猶如閃電般閃爍於作品表面,挑釁地挑戰作品表面的律則。形態與材質的二元分歧性,提供了創作者面對一個使藝術家著迷並將在未來的時日裡追逐尋覓的獨特課題。
但是進入了南藝研究所,侯連秦開始往跳脫其作品形態與自然形態之間細膩地連結關係。他直接且單純地專注於雕刻中形式、平面、表面與觸覺之間的互動關係。他緊緊抓住著雕刻藝術的精華,以它最高與最純粹的形式為之造形。現在的侯連秦,可以以其靈活又敏感的創造力,獨自飛行於藝術崇高的殿堂。對於一名研究所新生而言,這樣的成果簡直令人稱奇。
〝生〞,這是一塊大型而有紋路的長方形黑色大理石,中間斷裂處,似有無法制止的一股岩漿自內部噴湧而出,迫使石塊的腹部戲劇性地向上拱起,似乎表現著生育過程中所體驗子宮的極度收縮,好像能使得那塊笨重枕木般的全黑大理石突然在中端往上拱起來。
侯氏在軟與硬、直線與曲線、曲面與扁平面之間拉扯的張力中產生了無限活力,永遠在測試著觀者對堅硬石材的感受,並賦予它們生命,甚至流動性、動態和幽默感。在此處觀者同藝術家一起,沉浸於基本的雕刻藝術元素中:線條、平面、質地、顏色、動力和動態。我們一起體驗著這些基本元素在雕刻品中些微移動所帶來的整體動感。但是這種透過藝術品來連結創造者與觀賞者在精神上能合而為一的過程,只有在像侯氏一樣、有不凡天賦的藝術家出現以後,他們能為我們釋放出潛藏在這些堅硬石材中千變萬化的無數可能性,我們才有機會親自體會到這些活生生、美妙感官性的「藝術經驗」。
另一件白色大理石的作品,則以其毛茸茸的討喜外觀與質感吸引觀者的目光。作品表面因小結晶體的特質,而呈現出坑洞、穗花以及閃爍的視覺質感。猶如新落於山丘上的初雪,這件作品完全不沾染任何其他色彩,僅是純然的亮白質感。這件氣質內斂的作品,靜靜地邀請觀者的碰觸、撫摸,一旦觀者撫觸作品一連串的驚喜油然而生,手掌中的觸覺體驗將引領觀者繼續以遊移流轉的手感玩味作品,一路由頂端至底部透過觸覺感知作品那近乎完美的流暢與滑順,透過官能的體驗,觸覺將引領觀者走向內在的精神世界中。
侯連秦是一位對於未知的領域並不感覺畏懼的藝術家。他的作品中一再顯露出他對陌生世界的好奇心與欣喜。也許有人會問,在這個充斥著追逐名利與跟隨潮流的環境裡,以侯連秦這樣有著如此纖細敏銳感性的藝術家,如何能存活發展下來?天賦是一個答案,但更重要的是,只有當藝術家完全對於外界的雜音與干擾視若無睹、聽若無聞,完全滿足於其本身內在天空的伸展於無限的廣度,斯時,這種「真」的藝術天份方能完全真正的得到解放。
|